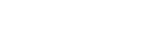周松:嘉峪关变迁与明代交通地理之关系——基于史源学的研究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明代嘉峪关是东西方陆上交通线的枢纽。但嘉峪关创建于洪武五年(1372)的说法于史无征,从史源学的角度看,实际出自明末的错误认识。冯胜西征结束后的20年中,明朝以军事胜利为前导,继之以军卫建设,终于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达成对河西全境的军事控制,嘉峪关创建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此时。永乐朝东西方陆路交通全面展开,使团往返不绝于路,延续至明末。期间,中国的官私史料,域外人盖耶速丁、赖麦锡、白斯拜克、鄂本笃等人都有涉及嘉峪关内外交通状况的记录。结合东西方对陆路交通的记载,加以比较分析,既可以相互印证,又能够发现一些史料缺载之处,明代嘉峪关交通地理的变迁得以明晰的展现出来。嘉峪关自身的变化反映了受畿服观念制约的明朝边疆控制模式的复杂性。明朝政治军事影响力是否溢出嘉峪关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便捷、效率与繁荣。
在长城史的论述中,人们特别强调山海关与嘉峪关作为明代长城起止点的重要地位。明代边墙(长城)的大规模兴建,乃至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实现于明代中期以后。明代早期的文献中很少提及嘉峪关,也没有建关时间的具体表述。但是,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洪武五年(1372)的冯胜西征,拓地至瓜沙,嘉峪关于此时建城,明朝统治了整个甘肃。[1]近年,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业已论证明朝获得河西走廊的稳固统治要到洪武朝末期。[2]然而,旧说影响颇大,来源不清,有必要以史源追溯法深入剖析,并基于此,从明代嘉峪关性质的演变探索影响亚洲内陆陆路交通的因素。
一、嘉峪关成于洪武五年说溯源
嘉峪关兴建于洪武五年的说法来自于冯胜的河西之战。然而考诸《明实录》及相关人物传记,并无证据。《明实录》称河西之战“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①]。傅友德的一些原始传记与此一致。[②]冯胜在河西之战中的事迹在《实录》中记载更详,谓“命为征西将军同大将军徐达分道征沙漠。兵至扫林山,与虏兵大战,斩故元平章不花等四百余人,降太尉琐纳儿加、平章管着等。进兵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以城降。次别笃山口,岐王朵儿只遁去,获平章长加奴等,牛羊马驼千余万。至甘肃,守将上都驴等率所部降,获吏民八百三十余户,马驼牛羊称是”[③]。其余传记大同小异。[④]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明军河西之战中采取了分道进击的方式。冯胜一路在走廊中部转向亦集乃地区;傅友德一路直接向西挺进,到达瓜、沙地区。大多数史料共同记载了战争中斩杀的敌人,获得降人、牲畜数量,但没有提到留兵驻守新占领地区的举措。唯独黄金声称,冯胜获胜后“分布戍守,扼塞关塞,乃还。”[⑤]但是此说极为笼统,既可以理解为在整个占领区派兵驻守,又可以视为在部分地区建立防御体系,难以成为有力的证据。
《皇明开国功臣录》成书于弘治十六年(1503),作者黄金这种含混的说法逐渐影响到之后对于河西之战战果的评价。同一时期的许进(1437—1510)曾参与收复哈密,正德元年(1506)致仕后撰《平番始末》。在此书中,许进认为“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河西。元守臣掠人民,遁入沙漠,遂略地至嘉峪关,而置甘州、肃州等卫。是即汉人断匈奴右臂之策也。”[⑥]第一次将冯胜西征与嘉峪关明确联系起来,使得傅友德“至瓜沙州……而还”的史实变为冯胜“略地至嘉峪关,而置甘州、肃州等卫”的“新论”。其子许论(1487—1559)则在《九边图论》中进一步发挥为“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下河西,乃以嘉峪关为限,遂弃炖煌焉。”[⑦]这样,就暗示了冯胜将嘉峪关作为明朝西部边界,嘉峪关的边塞形象由此树立起来。许氏说在万历时期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官方都得到了承认。万历本《明会典》载“国初下河西,弃炖煌,画嘉峪关为界。”[⑧]时人沈尧中也说“国初,宋国公经略河西,以嘉峪为限。”[⑨]因此,在万历时期,冯胜与嘉峪关的关系得到了朝野普遍认同。即便如此,整个明代并没有洪武五年建关的明确说法。
嘉峪关洪武五年建关说正式出现则是在清代。《重修肃州新志》云:“嘉峪关,在州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明初置。洪武五年,冯胜一河西,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西域入贡路必由此,筑土城,周二百二十丈。”[⑩]以此为起点,嘉峪关建关说遂为定谳,影响至今。
但是结合新出史料,分析洪武初年河西征伐的过程、实效,以及明初西北军事建置的过程中,则会认识到明初西北经略的复杂性、渐进性,进而动摇洪武五年建关说。那么,嘉峪关的建设应该在什么时间,需要结合史料深入探讨。
二、 明朝河西拓地与嘉峪关建造的时间
(一)洪武十年以前的明朝河西经略
洪武三年(1370)明军击败王保保之后,在黄河沿线确立自己的控制权。洪武五年,明廷兵分三路北伐元朝。其中,中路徐达、东路李文忠为主力,西路冯胜军作为疑兵,以牵制元廷军力。结果,徐达军大败,东路军也遭受重创。只有冯胜部所向披靡,兵锋遍及整个河西走廊。明人普遍认为“我太祖斥逐北虏,经略西陲。即命宋国公冯胜取汉武帝所开河西诸郡,以复古断臂之意。则此河西也,东起金城,西抵嘉峪,虽为一线之路,然北抗强虏,南护羌戎,岂不堑然华夏一大防哉!”[11]仿佛此战之后,明朝就控制了甘肃全境,实则不然。
明朝对三路北伐军赋予了不同的使命。朱元璋明确指出,“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12]正因为如此,冯胜军并未在河西聚歼元朝的有生力量,更主要的是驱逐敌军,瓦解破坏其防御体系。于是,冯胜军长驱直入,快速推进,后勤保障必然艰困,兵至瓜沙、亦集乃等地实属强弩之末。所以,听到“回鹘兵”的传闻,冯胜就立刻撤军。[13]对此,有学者推测为冯胜担心遭遇来自东察合台汗国的进攻,不得不弃守甘肃。[14]
但在另一方面,西征结束之后,明军越过了黄河,在黄河以北以西的地区建立了桥头堡,置立了庄浪卫等军卫,成为以后渐次经营的支点。
洪武七年(1374)“置凉州卫指挥使司,以故元知院脱林为凉州卫指挥佥事。”[15]《明史》称作“凉州土卫”[16],应为羁縻卫。九年(1376)年底,明朝“置凉州卫,遣指挥佥事赵祥、马异、孙麟、庄德等守之。”[17]
这就是说,直到洪武十年(1377),明朝在西北实际控制区仍局限于今武威及其以东地区。河西走廊中西部其时仍然处于残元部族割据势力的控制之下。那么,在明朝取得对整个河西走廊的控制以前,不可能越过北元活动区域(也可理解为瓯脱区),而在甘肃极西部建造孤悬于直接控制区之外的关隘——嘉峪关。
(二)洪武朝在河西走廊的系列战争
洪武十一年以后的13年中,明朝不断对河西走廊用兵,逐渐占据了整个走廊地区。
洪武十三年(1380)三月,西平侯沐英率领陕西军进攻走廊以北的亦集乃路。一战而胜,擒获其部众后返回。[18]另一路由都督濮英率领,出凉州,直趋河西走廊腹地的白城、赤斤、苦峪各地,大获全胜。沐、濮二军沉重打击了走廊西端的察合台后王集团,使得走廊东端已经没有蒙古集团的活动。明朝遂于洪武十四年(1381)在永昌设卫[19],明朝的边境线由此向西推进了856里。洪武十七年(1384),镇守凉州的明将宋晟再次攻入亦集乃路,战果惊人。明人对亦集乃路反复用兵的结果基本消除了北元经由此处南下的威胁。
北元覆亡之后,朱元璋意图招降哈密的兀纳失里王,[20]但是很快就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以哈密阻碍东西交通为由,出兵征讨。明军由凉州进发,出其不意,快速攻破哈密。[21]兀纳失里王逃脱,明军退回肃州。
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明军终于在在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至此,明王朝首次实现对整个甘肃地区的直接管辖,在此基础上探讨嘉峪关的建造才有了可能性。
(三)陕西行都司的全面成立与嘉峪关的建造
在明军袭破哈密之前的二十三年(1390),河西走廊的军卫建置明显加快,相继设立了山丹卫[22]和甘州左卫[23]。据明朝官修志书记载,甘州诸卫是在甘肃卫的基础上析置而成。此前扑朔迷离的甘肃卫当在二十四年成立于(或迁调至)甘州,二十六年(1393)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立于甘州,二十八年甘州五卫最终成立。[24]虽然甘肃卫和行都司调来时间为《实录》不载,但是甘州五卫的建置线索基本清晰。二十五年蓝玉西征阿真川,分置甘州中、右、中中三卫。[25]二十七年(1394),“改甘州左卫为肃州卫指挥使司,置甘州中中卫指挥使司。”[26]二十八年“改甘州中中卫复为甘州左卫指挥使司。初,陕西甘州置左右中前后并中中六卫,后改左卫为肃州卫。至是,以都指挥使陈晖奏,遂改中中卫为左卫。”[27]至此,甘州诸卫的置立方告一段落。
由此可见,嘉峪关关城的建造时间不能早于洪武二十三年,应该是在甘州左卫(即肃州卫)创立到二十七年肃州卫改置的过程中,作为肃州卫防卫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建造完成。具体说,嘉峪关的建造时间应该在1390——1394年之间。
从军事交通地理的角度看,“至兰州过河,至甘州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至肃州,又百里至嘉峪关,则舆图西边之极也。”“论曰:置邮传,命急务也。泛河西一路,直达嘉峪,羽檄飞驰,夜同清昼者乎?惟时加修葺,司兵居铺,则人文接递,庶无愆期耳。”[28]这是明人立足于疆域控制所发的议论。事实上,正是在明朝军队正式驻扎在肃州嘉峪关之后,西域诸国才真切的感受到明朝的实际影响,进而使东西方的交往迎来了又一新的时代。
三、永乐时代中外文本中的嘉峪关东西交通比较
永乐时期,不论明朝皇帝,还是中亚的帖木儿后王均先后派遣使者出使对方国家。东来西往的使节们必然途经嘉峪关,东西方官方旅行家的记载成为了解明代早期嘉峪关交通状况的一手资料。
(一)明代中国人的记载——《西域行程记》
明初,陈诚多次出使西域,留下了宝贵的旅行记录——《西域行程记》。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常客,陈诚的记录对于明王朝直接控制区内的路途没有特别留意描述。他笔下的旅程开始于肃州卫。从肃州卫出发到哈密为止,陈诚历时26天,除去中途短暂停留的6天,实际路途耗时20天,详情见下表。
嘉峪关虽为明朝西部边界,可是,永乐初年开始,明朝不断将关外大小政治集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据《实录》,永乐二年(1404),赤斤蒙古千户所已然设立,隶属肃州管辖[29]。同年,哈密正式内附,为忠顺王辖地。[30]三年,明朝又设立了沙州卫[31]。四年,正式设立哈密卫。[32]各地之间的关系为“赤斤,甘肃邻境也”,“沙州与赤斤接境”,沙州并不在交通主干道上,它的西北方向则为哈密。以此可知,嘉峪关外当属赤斤千户所辖区,赤斤以西当属沙州卫。如果结合《西域行程记》适可了解嘉峪关近边地区明朝的实际影响。该书涉及嘉峪关的行程仅有两天:“十六日,晴。早起,向西行。约七十里,至嘉峪关近安营。十七日,晴。过嘉峪关。关上一平冈,云即古之玉门关,又云榆关,未详孰是。关外沙碛茫然。约行十余里,至大草滩沙河水水边安营。”“二十日,晴。三更起,向西行约九十里,有古城一所。城南山下有夷人种田,城西有溪水北流,地名赤斤,安营。”[33]在嘉峪关和赤斤城驻留时,陈诚分别写下纪行诗《嘉峪山》和《经赤斤城》[34],对于两地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有所记载。陈诚离开肃州卫,出嘉峪关前,曾驻留祭祀,祈求西行安全。可见他将肃州嘉峪关视为明朝的西部边境。往后的行程中,没有看到明朝边防军在嘉峪关外乃至哈密一线活动的情况,甚至紧邻嘉峪关的地区也是如此。在陈诚记录中显示出,赤斤一带仍然是地广人稀的荒凉情景。陈诚离嘉峪关后,没有明军驻扎,表明赤斤、沙州卫是完全意义上的羁縻卫所,在永乐朝早期尚不能视为真正的明朝辖区,以此嘉峪关就成为明朝内边疆的分界线。
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出使之前,明朝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刚刚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考验。永乐北征后,在西起肃州,东达宁夏的整个河西地区短时间内出现了数次规模不等的变乱,时间从永乐八年迁延至十年,其中凉州变乱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永乐八年五月,凉州变乱初定之际,肃州卫又发生动乱。[35]所以,陈诚是在大乱初定之后不久出嘉峪关西使,同时期明朝的甘肃边军势必暂时处于守势,稳定河西政治秩序。这应是我们在《西使记》中看不到嘉峪关以外有明军活动和赤斤所(卫)记载的原因。陈诚对嘉峪关虽然没有具体表述,事实上却是汉文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文献证据。但陈诚一行并未在关城内住宿,而是选择过关出行,表明嘉峪关最初的规模有限,并不具备日后接待使者往返的功能。有学者论及洪武二十八年傅安自酒泉出嘉峪关后,造访西域,[36]实出自万斯同《明史》所载“安等于是出嘉峪关,西行八百里抵流沙”[37]。如果相信这一记载,则此为明代提及嘉峪关的最早直接证据。然而,傅安出使的原始文字记录应为他本人所撰《西游胜览》[38],但不见各种书目著录,久佚。目前所及,唯有明人曾棨(1372—1432)所撰《西游胜览诗卷序》引述傅著原文,谓“(傅)安遂由甘肃酒泉郡出玉关八百里,往流沙西北二千余里,至哈迷哩。”[39]时人孙瑀曾作《题西游胜览卷》诗一首,也有“昔年歌四牡,西出玉门关。遍历戎羌久,终持汉节还”[40]诗句,同样证明傅安本人所称出关之关为玉门关,而没有嘉峪关之名。
(二)明代中亚人的记载——《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无独有偶,中亚帖木儿帝国沙哈鲁派遣使团出使中国,使团成员同样留下详细的文字记载,其中,哈密至肃州一段特别提到了嘉峪关。
伊斯兰教历823年(1420,永乐十八年)7月25日,使团一行从柯模里(Qamul,哈密)启程,穿越大沙漠,直到8月12日抵达明朝边境。
“拉扎卜月25日,他们从那里(柯模里Qamul,哈密)出发,随后大部分道路都是穿越大沙漠,他们每隔一天或者两天才能得到水,直至他们在沙班月12日抵达一个经沙漠到肃州有十日程的地方,这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城市及他们的军事前哨。许多中国官员奉皇帝的命令前来欢迎使节。这是一个欢乐的草地。”[41]译者认为“过哈密后使者抵达的这个地方,可能在玉门一带。”对照陈诚出使路线逆推,哈密至嘉峪关实际用时20天。结合穿行大沙漠,水源紧张和距离肃州10天路程的的说法,我们怀疑译者的看法似乎太靠东。根据陈诚的记载,卜隆吉以西到哈密的道路沿途没有适宜宿歇的地点。唯有卜隆吉是“有夷人种田处,富水草”的地方。盖耶速丁接着说“拉扎卜(此处有误,应为大沙班)月16日(8月26日),使者们被告知,王大人当天要设筵。他是中国皇帝派守柯模里一边疆域的总督。从肃州到他的城市共九站。他曾率领一支五千到六千人的骑兵队伍出来迎接他们。使臣们都跨上战马,进向王大人的营地。”[42]它意味着明朝官员西行到卜隆吉欢迎使团,而且表明嘉峪关以西,卜隆吉以东已经有明朝军队常驻了。文中说道,从肃州到王大人驻在地有9站,如果以从东到西的方向理解,至卜隆吉恰好9个,再次证实我们的推断。作为外国使团,他们清楚的知道,王大人是明朝西部边境直到哈密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根据《明实录》永乐朝甘肃的总兵官先后是宋晟、何福、宋琥、李彬、费瓛,永乐十九年时费瓛在任。显然,接待使团的高官不是费瓛。永乐八年明朝以都指挥王贵镇肃州[43],到明仁宗即位后,升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王贵为右军都督佥事,仍旧镇守肃州[44],可见这位王大人当是王贵无疑,使团的记载非常准确。《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描述反映出自陈诚西使之后,明朝已经将军事活动的范围向西越出嘉峪关,甚至包括哈密卫在内了。
4天以后,使团受到王大人的宴请。“大沙班月17日(8月27日),他们继续他们穿过沙漠的旅行。几天内他们抵达一个叫做合剌瓦勒的地方。这个合剌瓦勒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四周掘有深堑:有条道路通过它,以此人们必须从一门进,从另一门出。当他们进入该堡时,整个队伍被清点,他们的名字被登记下来,然后从另一门出城。”[45]译者解释:“合剌瓦勒(Qarawal),波斯语义为哨兵,守卫,这里转为军事据点,关口。过了这个合剌瓦勒后即抵肃州,以此它当指嘉峪关。”译者的观点完全正确。使者们还注意到了嘉峪关城只有东西二门,远非现存嘉峪关城的建筑格局。这就是说早期嘉峪关极为简陋,仅仅起到边境检查点的作用。
由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准确记载了朱棣宠妃死亡和北京新皇宫被焚等事件[46],虽然具体时间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事件本身极为精确,完全可与《实录》相对应[47]。可以认为,该书对于嘉峪关记载的可信度很高。
三、明代中后期嘉峪关交通地理的记载
明代早期,置关西七卫,嘉峪关外直至哈密为明朝羁縻属地。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明朝边疆的最外沿。关外诸卫同时承担着为东西方使臣、商人和旅行者提供便利、帮助,防止劫掠行为出现的责任。所以这一时期,嘉峪关更多的表现为边防检查职责,军事防卫的特点不太明显。明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退,吐鲁番内侵,关西诸卫相继内迁,嘉峪关便成为明朝西部边防的最前沿。
(一)明人所载嘉峪关关城变迁
明代官方正式涉及嘉峪关的史料主要是景泰、天顺朝的两部地理总志:《寰宇通志》和《明一统志》。《寰宇通志》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明一统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明朝相隔5年就重新编订全国总志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因此,两书内容重复之处很多。《寰宇通志》称:“嘉峪山关,在肃州卫西六十里。其在城南又有文殊山、硫黄山、寒水石山、红山、观音山,凡五口。”[48]《明一统志》与此基本一致,唯独将“嘉峪山关”称为“嘉峪关”。[49]名称的差异将嘉峪关与附近山岗联系起来。《寰宇通志》载,“金山,在永昌卫城北二里。嘉峪山,在金山西,一名玉石山。”[50]两地相距过远,《明一统志》改为“金山,在永昌卫城北二里。又在故昌松县南,丽水出焉。”“嘉峪山,在肃州卫城西,一名玉石山。”[51]或许关名既得自山名。
嘉峪关最初形制狭小,绝非雄关。前面提到的中亚使者就将其描述为周围掘有深壕的城堡,东西两门,中有道路穿过。[52]《重修肃州新志》载,嘉峪关只是一座土城,“周二百二十丈”。所以,嘉峪关成为雄关有一个过程,诚如清人俞浩所言:“四面平川,关在坡上。坡下有九眼泉,冬不冻,夏不涸,饮万马而不竭。因有水而置关,因置关而建楼,因建楼而筑城。起卯来之南,而止于野麻湾之北。城筑于嘉靖中,肃州西面保障无过于此者。”[53]
随着明代中期关西诸卫逐渐衰落,纷纷内迁,其原有的捍蔽作用消失。吐鲁番政权不断东侵,使得嘉峪关完全暴露在直接军事威胁直下。由于嘉峪关军事重要性日渐凸显,原来的关城设施无法满足边防需要,必须大力强化关防建设。弘治七年(1477),明廷便“改作陕西肃州嘉峪关,易土以砖,扁曰镇西楼。”[54]这也就是说从洪武后期到弘治七年的百年之中,嘉峪关一直是以单一夯土城的建筑形式存在,1477年以后才出现砖墙、城楼,边防地位凸显。嘉靖十八年(1539)行边使翟銮才再度大规模加固城防,增设军马。[55]翟銮“由庄浪、凉州,越甘肃,直抵嘉峪关。是关为华夷之限。一关卑隘,既无城池,又极圮坏。每土鲁番犯顺,直至甘州镇城,杀掠人畜,若蹈无人之境。公阅视甚骇,曰:纵欲闭关绝贡,亦不可行。遂命肃州兵备具呈事宜。奏闻,得准修筑。恢拓坚固,城垣岿然,添设兵马。近年虏有犯甘肃者,此关扞御之功居多。”[56]《实录》称“行边使兵部尚书翟銮言: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而兵力寡弱,墙濠淤损,乞益兵五百防守,并修浚其淤损者。仍于濠内添筑边墙一道,每五里设墩台一座,以为保障。上从其议。”[57]具体的监造人是陕西参政李涵[58],二十一年完工[59]。此后,“(嘉靖)二十六年廵抚杨愽言,嘉峪关外先年止有近关大草滩、石烟墩、黑山儿三座。嘉靖八年添筑扇马城、上栢杨、下栢杨、回回墓、红泉墩台五座。今行相视,又宜于榆树泉、三条沟、火烧沟、古墩儿添筑墩台四座。隆庆二年,总督王崇古言,嘉峪关三面临戎,势甚孤悬,宜设守备防御。从之。”[60]至此,嘉峪关防御体系全部成型。
(二)明代后期中外文献所载嘉峪关交通环境的变化
嘉峪关军事作用的日渐增强是外卫内撤,藩篱尽失的结果。它带来的影响在于,嘉峪关外的东西交通状况急剧恶化,在相当程度上了影响了欧亚陆路交通的畅通。正如胡世宁曾言“况今哈密来至嘉峪关一带,千五百余里。其地先有罕东、齐勤(赤斤)等卫,原我属番,被彼驱胁供馈接应者,今皆归我欵塞。彼来所经,空地千里,供馈无资,又过流沙,水无所得。盖其入寇,比前益难。”[61]嘉靖十八年,严嵩也提到“历考书史,并询问夷使。西域地方自嘉峪关到沙州七百余里,沙州到哈密七百余里,俱系先年属番住牧,今已无人。”[62]
这一变化实际上在域外人的记载中也能看到。明朝末年,鄂本笃曾言“察理斯(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与支那之中间地,时有鞑靼人来侵,劫掠行旅。故商人经此者,莫不怀有戒心。日间先遣人自邻近山上探访,若无危险,道路平安,则于夜间潜行起程。鄂本笃等于途间,时见有回教徒商贩之尸身,横弃道上,盖为盗所杀也。”[63]很明显,在明朝的影响力收缩进嘉峪关之后,关外的东西方交通线风险大增。过往者即使采用塔里木盆地南缘,走于阗一线,仍无法保证路途安全。这是对东西方陆路交通严重障碍。换言之,只有处于中原政权控制下的陆路交通才能有效维系其正常运作。与海上交通线相比,此时已无任何优势可言。
意大利人赖麦锡[64]于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前后,引述波斯里海沿岸岐兰省(Chilan)陀拔思城(Tabas)商人哈智摩哈美德的见闻。哈智摩哈美德声称他曾亲身访问过肃州,并且说“若由去时之道而归,则情形如下:离甘州至高台(Gauta)六日程,……由高台至肃州五日程。由肃州至哈密(Camul)十五日程。由此以东,皆拜偶像者之境域,以西则回教徒之地矣。”[65]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嘉峪关,但是却反映了吐鲁番东侵后民族文化格局的变化。荷兰人白斯拜克[66]又在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记载了一名土耳其人的东方见闻,提及“终乃抵一小隘,契丹国边境之关塞也。其国大部分皆为平原内地。近关处有连山,崎岖危险,不通行人。仅此一隘,可以通行。国王遣兵驻守之。”[67]这是明后期最有可能直接记载嘉峪关的外部史料。然而就其内容分析,则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相似,仿佛仍是明朝中期以前的印象。
明末的1604年,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1562—1607)“由哈密行九日,抵支那国北方之长城。此城世界著名。停留处曰嘉峪关(Chiaicuon)。在此休息二十五日,以待是省总督之回音,可否入。至后,总督覆音许入,于是起身。行一日抵肃州(Sucieu),在此闻得北京及其他以前所知各地名。至是时,鄂本笃心中最后怀疑始全去,契丹即支那,同地而异名而已。”[68]在鄂本笃口中,嘉峪关是著名的交通枢纽,已经具有接待往来使客的能力,显示出到明朝后期,嘉峪关的地位才脱颖而出,成为明朝西部的边防重镇和交通中心。也只有到此时,西方人才确定来自大陆方面原指中国北方的“契丹”和来自海洋方面对中国的“支那”称谓事实上都是中国。海洋观念和大陆观念终于结合在一起。[69]
四、明代嘉峪关交通地位变迁之原因
明代史料极为丰富,但分布不均,前少后多,辗转因袭。在《实录》流入民间之前,有关明初的史事多不得其实,往往以臆说沿袭,遂成定论。就洪武朝的西北经略而言,其实质就是以明朝的统治取代元朝的统治,这一更替过程以军事斗争为前提,以军卫建置为基础,以完整的控制体系建立为标志。洪武五年冯胜西征河西走廊,事毕,全军撤出走廊,仅起到了驱赶元军的作用。其后随着多次军事行动的胜利,伴以军卫置立逐渐西进,方才形成对河西全境的军事控制。洪武后期陕西行都司迁往甘州和肃王正式就藩后,整个边政体系才得以建立。明代后期对于明初西北经略史的认识已经模糊不清,总的倾向是以某件重大事件作为经略标志,所以才有了洪武五年控制整个甘肃以及相应的嘉峪关建关说。显然,明人以后出的史料解释早期史实,忽视对《实录》的分析,违背了史源学的原则,最终导致了错误的认识。这一误解又被清人承继下来并且影响至今。对嘉峪关建关时间的重新确定并不影响其在明代边防和内陆交通史上的地位。讨论嘉峪关建置及其自身演变是为了厘清明代亚洲内陆交通的盛衰与明朝边疆管理方式的内在联系。
(一)嘉峪关性质的变化是明代治边理念的反映
传统的看法认为嘉峪关的性质是明代西部陆地边界的最前沿,但是明代的观念与此有很大差别。《雍大记》即称,“(洪武)二十六年立陕西行都司指挥使司,治甘州五卫,领肃州、山丹、永昌、凉州、镇番、庄浪、西宁、沙州一十三卫,高台、镇夷、古浪三千户所,并赤斤蒙古、哈密、安定、罕东、曲先、苦峪六羌胡羁縻卫所。”[70]很明显,明人将西北地区的普通实土卫所与羁縻卫所整体视为陕西行都司的下属军事单位,根据这种认识,陕西行都司的西部边界当处于哈密与吐鲁番之间。这不是孤立的观点,而是明朝的共识,《陕西通志》亦称,“雍人曰:愚闻春秋之道二,曰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也。谨华夷之辨者,王道之用也。我祖宗朝设立河西疆域,西抵沙州、哈密,北为胡虏,西为吐番,通其贡赋者,王德之体也。正其疆界,慎固封守者,王道之用也。”[71]这种情况下,嘉峪关边关作用无从体现。另一方面,明朝将嘉峪关作为盘查入明域外人的关口,甚至称为“华夷之限”、“中外巨防”,又给人以边疆前沿的感觉。两相比较则会看到,嘉峪关以西至哈密、沙州一线在明人的理解中并不完全清晰。
关外诸卫是对明朝西北直接控制区的藩蔽,是介于内边疆与外藩之间的过渡区,其与外藩的边界可视为明王朝的外边疆。明朝虽然在嘉峪关外设立关西七卫,但均为羁縻军卫,军卫本身大小不一,军卫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军卫长官的封授、承袭、擢拔必须报经朝廷批准,而军卫内部事务,明廷很少干涉,这与内地军卫迥然不同。若以今天的边疆概念看待,则会发现明朝的西部疆域不出嘉峪关。但是这样根本无法反映出明朝政治、军事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实际表现。从军卫设立看,内地式军卫的分布地区就是明朝的直接统治区,在直接统治区之外,尚有间接统治区,间接统治区之外才是藩属政权。嘉峪关外直至哈密就是这样一个间接统治区,那么嘉峪关就是明朝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分界线。
明代中期在以吐鲁番为代表的外藩冲击之下,明代西北边外持续存在各种政治势力矛盾加剧,明朝控制影响的难度空前增加。因此,一旦明朝国力衰退,军力收缩,就会放弃外边疆,原来的间接统治区也会为藩属政权占据,从而使内外边疆重合。那些羁縻军卫迁入嘉峪关内,这也证明了他们与明朝之间始终存在着更为紧密的依附关系。内边疆——外边疆——外藩——远夷形成的圈层结构这一解读本身是基于西方视角对中国历史上华夷关系的地理认识。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看,不妨理解为畿服理想统治模式在明代中国的现实化。
(二)明代西北“外藩”的历史变迁是影响陆路交通的重要外部因素
明代亚洲内陆交通线的西部连接着广大的新疆、中亚、西亚地区,即明人所称之“西域”[72]。陕西行都司“控制边境远番,若柳城、哈剌火州、土鲁番、剌竹、别失把里、撒把儿罕、黑楼、失剌思、亦思不罕、帖卜列思,皆由是路入贡焉。”[73]在14—17世纪,中亚地区虽然出现过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汗国等大国,但政权的统一完全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雄才,所以大多数时候,中亚地区在政治上是以分散割据面貌呈现出来。新疆地区先后出现的东察合台汗国与叶儿羌汗国,其政权形式表面上维持着汗权名义的统一,实则是宗室、地方贵族联合统治,其间相互倾轧,矛盾冲突不断。加之,宗教活动强化,民族集团迁徙、融合,遂使这一地区长期处于政治混乱之中,碎片化倾向显著。所以在明代史籍中记载新疆中亚地区常常出现的“地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此政治特点的反映。与汉唐时代截然不同,由于从未对明朝构成实际威胁,所以自明初立国起,西域就不曾是明朝对外军事活动的重点区域。明朝中后期对于西域内部的变化既不关心,也不了解,“迤西,大则撒马儿罕、天方国、鲁迷、亦郎,小则黑娄、怯迷、阿即民、沙密、把黑旦等处,即汉之车师、康居、大宛之属。随代易名者,皆由土鲁番之地始可达于中国。今其人至,虽云各国名色,缘各夷面貌语言相类,真伪难辨。节年差人止到土鲁番,夷西诸国皆未曾到。西域动静虚实皆不能真知。”[74]
更主要的是,在中亚、新疆“随着国家的分裂和游牧人的不断入侵,农业也衰落了。”[75]尽管在特定区域内部,商业市场呈现了出繁荣景象,但总的来看,与历史时期相比,农业经济的衰落、商业贸易的消沉是其基本状况。西域各政权深处亚洲腹地,迫切需要与周边地区开展经济往来。当他们的内部斗争没有影响到明朝边疆稳定时,大陆交通保持畅通。一旦斗争外溢至“属蕃”,甚至边境之内,明朝不愿发兵远征,通过军事手段恢复原有秩序时,只能采取“闭关绝贡”进行制裁。如此则造成了陆路交通的退化,这是其外部原因。
(三)明朝西北治边方式的两面性固化了西部边疆
明代对边远地区的控制是通过军事移民的方式实现(如甘肃、云南等地)。军户群体本地化是维持明朝对新占领地区实施直接控制的基础。再者,明朝辽东、甘肃、川西等边远地区采用行都司这一军政式的地方管理体制,领有实土,兼理民政具有扩大稳固疆土的独特作用。[76]
但即便如此,在明人看来,西北地区仍未恢复汉唐旧疆。“捐沙州及哈密之地于蕃而设关于肃州嘉峪之地,已非旧矣。迩年以来,吐蕃之人、方物之贡常通,乃归至甘肃之境,辄居而不行。今二州所居番人盈城遍野。”[77]显然,在行都司所辖的河西走廊,不仅仅只有军户和当地土著后裔,更有西域人士普遍分布,人口构成多样化。于是,有人“言今番人居内,疆域虽与我同,而政教实不加焉,亦非覆载之意”[78],主张一概进行儒家文化教育,科举取士,广纳文武人才,以收安定边疆,增强国力之效。“沙州即古炖煌地。其人材自古为盛,光馥简编。今其人何独不然,作新之以复古,以安疆,亦在乎人耳。诚如是,则无弗覆载之中,用亦备矣。不然,听其自如,则苟安之计,吾知冰炭同器,不濡则然。非惟中国不宁,彼亦岂能安耶?”[79]必须承认,这一说法颇有见地,但是依靠旧的行都司管理体制很难实现这一目标。
洪武后期明朝在甘肃建立行都司体制之后,延及明亡。这一基本地方统治架构固化为某种政治思维定式,最终落入了固守祖宗成法的窠臼。随着人口的迁徙,社会的发展,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改行完全内地化的军民分治管理模式,推动边地社会与内地社会趋同,方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统一。明朝没有随着国势的变化,以民政体制替代军政体制的工作,最终被清朝完成。清朝建立之后,经过短期过渡,于康熙二年(1663)分省甘肃,八年(1670)正式设置甘肃省。至此,甘肃才真正完成了与内地的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清代边疆地区的五大将军辖区,某种程度上与明代行都司体制有军政统治类似之处,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完全统一。
总之,明代嘉峪关为界,以内体现的是明王朝一体化统治模式;以外体现的是明王朝的国家影响力: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实力的控制和影响,二是国家软实力的声望辐射。两者共同为亚洲陆路的正常运行、畅通和繁荣提供了保证。国家影响力受传统畿服之制与民族关系的多重影响,在明朝国力的下降之后,将嘉峪关的功能全面整合(从单一走向复杂),边防的军事作用日渐凸显,内外边疆的合并。明王朝的注意力被国家安全所吸引,主导亚洲内陆交通发展已力不能逮。
参考文献:
[①]《明太祖实录》卷74,洪武五年六月戊寅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1538—1539页。
[②]参见[明]黄金撰:《皇明开国功臣录》卷5,收入周骏富编辑:《明代传记丛刊》第23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影印本,第356页。[明]袁袠撰:《颍国公傅友德传》,收入[明]焦竑编辑:《国朝献征录》卷6《公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97页。[明]郑晓撰:《吾学编》卷24《皇明名臣记卷三·太子太师颍国傅公》,《续修四库全书》第4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412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236,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丁卯条,第3450页。
[④]参见[明]王世贞撰:《宋国公冯胜传》,收入[明]焦竑编辑:《国朝献征录》卷6《公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93页。[明]刘三吾撰:《大明勅赐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宋国公同参军国事冯胜追封三代神道碑并序》,收入氏著:《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120—121页。《吾学编》卷18《皇明异姓诸侯传》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4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86页。
[⑤]《皇明开国功臣录》卷1,收入《明代传记丛刊》第23册,第177—178页。
[⑥][明]许进撰:《平番始末》,《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59页。
[⑦][明]许论撰:《九边图论》,《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03页。
[⑧][明]申时行等修,[明]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130《兵部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323页。
[⑨][明]沈尧中辑:《沈氏学弢》卷9,明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3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558页。
[⑩][清]黄文炜、沈青崖纂修:(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十一册》,《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233页。
[11][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04,《续修四库全书》第16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42页。
[12]《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甲戌条,第1322页。
[13][明]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64页。
[14]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243页。
[15]《明太祖实录》卷93,洪武七年十月甲辰条,第1627页。
[16]《明史》卷42《地理三》,第1015页。
[17]《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九年十月戊寅条,第1823页。
[18][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5—26页。《国朝献征录》卷5《公一·黔国公沐英传》,《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第146页。
[19]《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条,第2259页。
[20]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98,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子条,第2977—2978页。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02,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未条,第3023页。
[21]《明太祖实录》卷211,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亥条,第3138页。
[22]《明太祖实录》卷204,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庚寅朔条,第3051页。
[23]《明太祖实录》卷206,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条,第3075页。
[24]参见[明]陈循等撰:《寰宇通志》卷201,《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7册,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17—318页。
[25]《明太祖实录》卷217,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辛未条,第3193页。
[26]《明太祖实录》卷235,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巳条,第3433页。
[27]《明太祖实录》卷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乙酉条,第3477页。
[28][明]恽应翼修,张嘉孚纂:《(万历)新修安定县志》卷1,《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39卷,兰州古籍书店年1990影印本,第9,17页。
[29]《明太宗实录》卷35,永乐二年十月辛未条,第610页。
[30]《明太宗实录》卷32,永乐二年六月甲午条,第573页。
[31]《明太宗实录》卷47,永乐三年十月癸酉条,第720页。
[32]《明太宗实录》卷52,永乐四年三月丁已条,第787页。
[33][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校注本,第33页。
[34][明]陈诚撰:《陈竹山先生文集·内篇》卷2《西域往回纪行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337—338页。
[35]详见《明太宗实录》卷104,永乐八年五月丁亥,第1352—1354页;《明太宗实录》卷107,永乐八年八月壬戌,第1391页。
[36]万明:《明初中西交通使者傅安出使略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0年第2期第31页。
[37][清]万斯同撰:《明史》卷182,《续修四库全书》第3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391页。
[38]注:该书又名《使远传》(见杜鸿宾修、刘盼遂纂:《太康县志》卷5《艺文志上》,《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六六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版,第280页),俱不见传本。
[39][明]焦竑编辑:《国朝献征录》卷80《六科都给事中·南京六科给事中》,《续修四库全书》第5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298页。
[40][明]孙瑀撰:《岁寒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版,第45页。
[41][波斯]火者·盖耶速丁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107页。
[42]《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07页
[43]《明太宗实录》卷109,永乐八年十月己亥条,第1405页。
[44]黄彰健著:《明仁宗实录校勘记》卷4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第65—66页。
[45]《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10页
[46]参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34—135页。
[47]《明太宗实录》卷235,永乐十九年三月甲申条,第2260页;卷236,永乐十九年四月庚子条,第2263页。
[48][明]陈循等撰:《寰宇通志》卷101,《玄览堂丛书续集》二辑十七册,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27页。
[49][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37,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655页。
[50]《寰宇通志》卷101,《玄览堂丛书续集》二辑十七册,第320页。
[51]《明一统志》卷37,第653,654页。
[52]《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110页
[53][清]俞浩撰:《西域考古录》卷5,《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602页。
[54]《明孝宗实录》卷84,弘治七年正月辛亥条,第1578—1579页。
[55]参见《明世宗实录》卷221,嘉靖十八年二月壬寅条,第4573—4574页;卷224,嘉靖十八年五月戊辰朔,第4641页。
[56][明]许成名撰:《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石门翟公銮行状》,[明]焦竑编辑:《国朝献征录》卷15《内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46页。
[57]《明世宗实录》卷229,嘉靖十八年九月丙申条,第4731页。
[58]《明世宗实录》卷236,嘉靖十九年四月壬申条,第4818页。
[59]《明世宗实录》卷260,嘉靖二十一年四月戊午条,第5189页。
[60](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十一册》,《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233页。参见《明世宗实录》卷328,嘉靖二十六年闰九月丁亥,第6042页。《明穆宗实录》卷34,隆庆三年闰六月辛亥条,第880页。
[61][明]胡世宁撰:《回人入境官军击斩退去随逓番文讨要羁留夷使疏》,《胡端敏奏议》卷10,[清]纪昀、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34页。
[62][明]严嵩撰:《南宫奏议》卷29《夷情四·议处甘肃夷贡》,《续修四库全书》第4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493页。
[63]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4页。
[64]注:赖麦锡(Giambattista Ramusio,1485—1557)意大利地理学家。
[65]《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60页。
[66]注:白斯拜克(Auger Gislen De Busbeck,1520—1592)荷兰人佛兰芒人,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出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67]《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69页。
[68]《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434页。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
[69]注:明代的海上和陆上交通承载了西方人头脑中两个东方大国的形象:支那与契丹。在两个观念重合之前,说明海上和陆上交通在向西延伸的过程的中并没有出现交集和交流。但是,在西域人看来,从海上和陆上都能够到达明都北京,如:弘治二年中亚撒马儿罕阿黑麻王遣使取道马六甲,到广州进贡狮子、鹦鹉。(《明孝宗实录》卷32,弘治二年十一月壬申条,第717—718页)弘治三年,土鲁番也派使臣哈只火辛从海道贡狮。(《明孝宗实录》卷43,弘治三年闰九月丁酉条,第884—885页)
[70][明]何景明撰:《雍大记》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50页。
[71][明]赵廷瑞修,[明]马理纂:(嘉靖)《陕西通志》卷6,《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一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影印本,第126页。
[72]《大明会典》载,“嘉峪关外并称西域。而陕西以南并四川,抵云南外徼,并称西番。”(《大明会典》卷107《礼部六十五·西戎上》,《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92页)
[73]《雍大记》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4册,第50页。
[74]《南宫奏议》卷29《夷情四·议处甘肃夷贡》,《续修四库全书》第476册,第493—494页。
[75]M.S.阿西莫夫、C.E.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4卷(上),北京:中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页。
[76]参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77][明]赵廷瑞修,[明]马理纂:(嘉靖)《陕西通志》卷六,《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一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影印本,第126页。
[78]同上。
[79]同上。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有疑问?
文章没看明白?还有疑问?您还可以通过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收到留言后第一时间联系您。
姓名:电话:
疑问:版权声明
1、本站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
2、文章部分图片及信息来源于网络,文字与部分图片之间无必然联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3、我方无意侵犯某方的知识产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