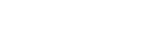《新加坡与中国新移民:融入的境遇》序
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合力创办的南洋大学,其华裔馆、中文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使这所国际化的国立大学仍延绵着其创始的初心,甚至成为老华侨华人眼中的文化象征。游俊豪教授身兼三任,同时执掌这三大国际学界重镇,却依然学术成果丰硕。《新加坡与中国新移民:融入的境遇》一书就是其最新成果。有幸先睹为快,感佩有加。俊豪教授出生于马来西亚,成长于新马,温文尔雅,性情敦厚而才华横溢,其中华传统文化的士人情怀;同时其熏染的西方文化与马来文化,又自然散发出多元文化与国际范的气质。文如其人。本书的视角不同于西洋学者,也不同于中国学者,俊豪教授以一个南洋华裔学者的身份研究中国新移民,并由此出发探讨移民理论。作为中国大陆学者,受益良多。本书立意高远,其绪论开宗明义,要探寻新加坡“本土语境如何因应全球化的冲击与影响,国家体制如何规划移民的流向与存在,历史话语如何反映身份认同的转变。” 因为中国新移民1990年后骤增,在新加坡紧凑的空间和结构里,冲击的力度让在地社会感受特别强烈。作者从身边的鲜活故事和案例去升华移民理论,并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置入作者的学术体系之中,更能完整的理解作者的解释框架,从历史脉络和华人族群中更好地把握中国新移民的特点。2014年作者出版了《移民轨迹和离散叙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好评如潮。两部著作相辅相承,分合自如,相得益彰。全书结构简单明快,层次清晰而生动,逻辑严密,浑然一体。第一个层面是身份与族群。将中国新移民置于新加坡华人移民历史脉络之中述其渊源流变,从文化互动的过程中究其身份认同与族群特征。无论是新移民作为族群的生活习惯,或者新移民作为个体的行为作风,主流社会对此时有成见,甚至不无刻板印象。这需要主流社会与中国新移民协力合作才能消弥,以促进融合。第二个层面是结构与组织。一方面探讨中国新移民与主流社会和国家的关联,既包括移民在各层面的融入,也包括国家在各族群中的资源配置。多元化的新移民体现了分层融入的进程,分为向上、平行、向下三种主要路线,分布在当地社会的各个阶层。另一方面探讨新移民群体内部的组织特征。在贴近在地脉络方面,新移民团体积极跟主流社会团体合作,主动举行慈善活动,致力于跨文化跨族群的互动。在建构跨国主义方面,新移民面对史上全新的中国,一个崛起的富强的中国,面对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新加坡,自然就努力推动新加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文化交流也更为丰富。新移民社团,不但促进会员之间的情谊,而且为在地华社注入新的活力,并跨出族群的边界,进行更广泛的交流。第三个层面是群体案例:学生、陪读妈妈、作家。这三个群体各自体现出相关联的移民生活次序,学生反映过渡,陪读妈妈反映挣扎,作家反映主体性质的多元,也反映移民融入的不同路径与层面。作者从这三个熟悉的群体,信手拈来,娓娓道来,在人类学的感性体验与追踪调研基础上,又有严谨的问卷调查和科学论证。人们通常熟视无睹,对久处身边的人与物,反而缺乏感觉;在俊豪的笔下,却能细腻感知新移民在新加坡的分层融入,又能在其整体框架下获得学养提升。俊豪教授亦是知名作家,其文字平实干练,又能行云流水般揭示深遂的内涵。当然,对中国读者而言,大陆与海外存在语言表达习惯的一些差异,不过,几乎没有阅读障碍,反而体现了语言表达的多样性。新加坡是我进行学术交流与调研次数最多的之一,不下十次。我有幸接触过本书论及的新加坡清华校友会、天府会、华源会等新移民社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宗乡总会、义安公司、同济医院等传统社团;我们也到访过不少南洋顶级富豪的新加坡豪宅。拜读俊豪教授新著,引发共鸣,受其启发,从比较视野与中国视角谈一点研究体会。对于中国新移民,除了在新加坡与东南亚各国有所接触之外,我在美国、加拿大进行过多次深度调研,也实地考察过英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日本、韩国甚至南非的移民、侨商及其社团。相比较而言,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独具特色。就新移民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新加坡有某些有利之处,但其不利因素更多更普遍,因为创业与就业的空间有限。从这一视角出发,移民的生存发展特别是其经济成长,取决于如下因素:差异性、规模化、中介性、民间性或市场化。其一,差异性或边缘性,是指移民的独特性与主流社会存在较大差异或落差。一方面移民迁徙至异国他乡,具有不可替代性,能够在当地经济与社会中填补空白;另一方面,相对于主流社会来说移民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但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美国,华人在边缘与前沿中成长。边缘成长的代表是偷渡客,他们在美国人不愿意干的低端就业市场艰辛劳作,站稳脚根,便开始以中餐馆、杂货店等低门槛创业,进而拓展至亚洲超市或族群银行之类,在经济缝隙中寻找利基,以其差异化实现财富创造,并可能逐渐壮大跻身主流。岛国新加坡几乎不可能存在偷渡客,中国新移民在边缘寻求差异化创业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前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边缘,主要体现在科技产业、金融业等新经济前沿,美国金融市场发育孵化出中国、印度等移民科技企业。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也有不少活跃于科技领域。与边缘相对是主流或核心,二战以后的东南亚各国,华人在新兴的工业化进程中逐渐举足轻重,成为民间经济的主导或中坚,这主要是因为原住民农业族群为华人企业家留下了工业化的空白,使华商大显身手而茁壮成长。新加坡亦然,但1990年后新加坡中国新移民面对的是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行业与市场格局基本定型,不可能重现历史。其二,规模化与拓展性。移民经济与社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或呈网络化存在,才能形成自生与自我扩张能力,从而形成持续发展的活力。世纪之交美国华人大巴新模式,就起源于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唐人街的人员与货物流动,进而在竞争中形成城际大巴新业态,并走向主流。如果没有1990年代以来新移民的持续涌入,唐人街经济就不能扩大与扩散,华人大巴新业态就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从边缘走向主流。族群经济如果不成规模,或不能形成网络,则只能星星点点散落各地,难以自我生成活力,可能不久就会自生自灭,更难以形成拓展力。新加坡岛国的新移民难以形成规模性发展。其三,中介、桥梁或跨国化。移民以其连接祖籍国与移居国的优势,企业家精神得到激发和释放,中介跨国文化交流与贸易。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贸易型华商是其典型,依托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打开各地市场。本书也揭示了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这种角色与作为。其四,民间性与市场化,这是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移民是一种跨国的自发流动与选择,只可能依赖民间途径与市场机会,政府安排只存在于极端情形。如果政府控制强,民间机会少,不利于新移民自谋生路。事实上,从出境到入境,从谋生到发展,世界各地的中国新移民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与银行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移居国政府的额外扶持,相反要克服各地政府的重重障碍。二战前的东南亚殖民地时期,政府控制较弱,殖民经济开发也需要吸引移民。源源不断涌入的华侨华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较大的生存空间,还形成自治性组织。就移民社团与社区秩序而言,外部压力越大,族群独立性越强,自我保护的诉求越强,社团与自组织就会越发育。历史时期南洋、北美,就形成相当强的族群经济与社区(ethnic economy and society),甚至曾有一些封闭性的社区,华人社团成为自治社会的枢纽与中坚,不少社团还成为新移民生老病死的依托。事实上,中国移民的自组织能力,在中国具有深厚的传统。与朝廷对官僚体系的严密控制形成鲜明对照,清政府对基层的取向大体是自由放任的,民间社会发育的潜能与空间较大。民间社团丰富多样,自组织能力较强,基层秩序呈现自治色彩。二战前中国移民到达的南洋各殖民地,小政府多族群,殖民政府对华人与马来人等实行分而治之,更使华侨华人自治能力得到充分释放。当今新移民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大大淡化,新加坡尤其如此,移民社团的功能发生转变,移民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历史的纵向比较,还是地域的横向比较,与上述共性相对照,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具有其鲜明特征,除了本书所论之外,以下几点感触颇深。首先,新加坡秩序井然,政府就像一个无微不至的保姆,对新移民而言,社会与市场自发成长的空间反而受到一定限制。其次,新加坡经济发展成熟,行业格局基本定型,国内市场狭小。自生自发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行业难以萌生,破茧而出,新移民经济的自生能力极为有限。再次,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的族群与文化差异,相比华人与其他种群的差异来说毕竟较小,移民进入主流的障碍相对较小,但移民发展容量有限,因此不可能形成美国所出现的依赖移民的不可替代性与市场利基而获得发展,移民经济难以开创拓展性空间。此外,在新加坡自成一体的移民经济形态几乎不存在,更谈不上规模,因而不像美国华人经济达到相当的规模,具有自我生成与自我扩张能力。本文与其说是一篇序,不如说是拜读俊豪新作之后的感想、启发和收获,与读者分享。
有疑问?
文章没看明白?还有疑问?您还可以通过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收到留言后第一时间联系您。
版权声明
1、本站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
2、文章部分图片及信息来源于网络,文字与部分图片之间无必然联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3、我方无意侵犯某方的知识产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